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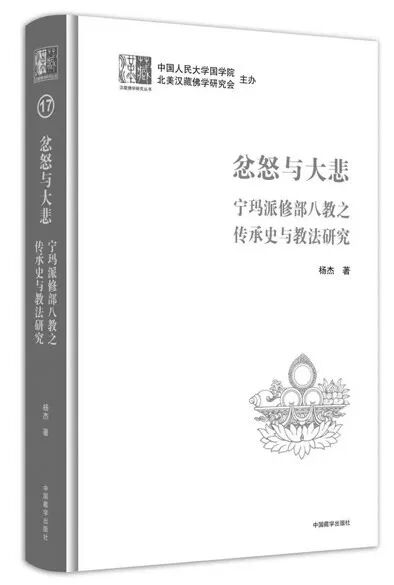
《忿怒與大悲——寧瑪派修部八教之傳承史與教法研究》,楊杰著,中國藏學(xué)出版社即出
千呼萬喚始出來,楊杰博士的大作《忿怒與大悲——寧瑪派修部八教之傳承史與教法研究》終于要和廣大讀者見面了,可喜可賀,可贊可嘆!雖然它有點姍姍來遲,但凡屬名山之作,皆值得我們耐心等待。楊杰這部著作的基礎(chǔ)是他十年前完成的博士論文,其實,它在當(dāng)時或就已經(jīng)達到了可以出版的學(xué)術(shù)水準(zhǔn)。或是出于對學(xué)術(shù)和教法的雙重敬畏,或是出于對職業(yè)和人生之理想境界的執(zhí)著和不懈的追求,他硬是將之束之高閣,貌似置之不問,實則一頭潛入法海深處,凝然安住,細細打磨。十余年間,懸梁刺股不足以譬喻其意志之堅定,手不釋卷不足以比擬其學(xué)業(yè)之精進,面壁十年圖破壁,于今所求所愿,悉皆圓滿,所修所習(xí),皆得自在!這部《忿怒與大悲》雖非楊杰學(xué)術(shù)之全部,卻足夠典型地顯現(xiàn)了他這些年來所習(xí)之道果和所得之成就,它的出版是他研究藏傳佛教之學(xué)術(shù)生涯的第一座里程碑。十年磨一劍,出鞘露鋒芒,不鳴則已,一鳴驚人!
于博士畢業(yè)之后這十余年間,楊杰一如既往地潛心于學(xué)習(xí)和研究藏傳佛教寧瑪派的教法與實踐,專注于翻譯、注解寧瑪派等各派上師們的經(jīng)典著作,以歷代“摩訶啰拶咓”(大譯師)為楷模,譯筆不輟,至今譯注的藏文佛教經(jīng)典著作已逾百余萬字。他對寧瑪派的歷史、教法和宗教實踐都有極為全面和深刻的理解,無疑是當(dāng)今世界寧瑪派研究之頂級青年學(xué)者。他幾乎以一己之力,編纂了一部百余萬字的巨著——《大圓滿與如來藏——寧瑪派人物、教法和歷史研究》,匯集國際寧瑪派研究之精粹于一冊,為寧瑪派之歷史和教法的研究、傳播作出了巨大的貢獻。與此同時,楊杰學(xué)而不厭,誨人不倦,十分熱心于學(xué)術(shù)授受,他利用中國人民大學(xué)國學(xué)院漢藏佛學(xué)研究中心這一特殊的學(xué)術(shù)平臺,日復(fù)一日,年復(fù)一年,為來自北京各大高校和學(xué)術(shù)、科研機構(gòu),以及社會各界愛好藏語文與藏傳佛教的學(xué)生們,開設(shè)了許多程度不同、題材各異的藏文佛教文獻閱讀和研究課程,傾注了大量時間和心血,培養(yǎng)了一批批有志于學(xué)習(xí)和研究藏傳佛教的青年學(xué)術(shù)人才。
當(dāng)然,楊杰未忘初心,對寧瑪派修部八教的研究始終予以最深切的關(guān)心。十余年間,他不斷擴充乃至窮盡對相關(guān)藏文資料之搜集整理,力求全面把握修部八教傳承的歷史,把修部八教的教法和修習(xí)放置于整個寧瑪派,乃至整個印藏佛學(xué)的學(xué)修體系和歷史語境之中,作細致入微的考察和研究,并及時吸收國際學(xué)界的最新成果,絕對不落人后,與時俱進,保證自己的研究與世界學(xué)術(shù)之最新動向同步前行,且有過之而無不及。尤其值得稱道的是,他的文字表述簡單明了,如行云流水,起承轉(zhuǎn)合皆恰到好處,幾臻完美;而他的義理闡發(fā)則甚深廣大,智慧方便雙運,遂令學(xué)術(shù)和宗教圓融無礙,相得益彰。無疑,《忿怒與大悲》是近年所見藏傳佛教研究作品中一部難得的上乘之作,我有幸先睹為快,不勝欣喜,故于此略贅數(shù)言,以作莊嚴(yán)慶贊!
藏傳佛教之“舊譯密咒”,或曰寧瑪派,與“新譯密咒”形成對照,二者乃藏傳佛教傳統(tǒng)最主要的內(nèi)容,也是藏傳佛教研究最核心的組成部分。國際學(xué)界對寧瑪派的研究開始較早,也已經(jīng)有了不少出色的研究成果。但是,迄今為止,寧瑪派研究的重點主要集中在對于已在西方世界流傳甚廣的“大圓滿法”的研究,和對被認(rèn)為是寧瑪派祖師之蓮花生大士的研究之上。成果最突出的是利用敦煌出土的古藏文文獻展開的有關(guān)“大圓滿法”、蓮花生崇拜,以及早期摩訶瑜伽流傳的歷史和它與中土禪宗之關(guān)系的研究,如杰出的藏族學(xué)者卡爾梅·桑木丹教授的名著《大圓滿——藏傳佛教的一個哲學(xué)與禪修教法》(The Great Perfection: A Philosophical and Meditative Teaching in Tibetan Buddhism)等。但是,對于藏傳佛教后弘期正式開始之后,寧瑪派傳統(tǒng)之形成和發(fā)展的歷史過程,學(xué)界至今缺乏廣泛而深入的研究作品。而寧瑪派于其形成和發(fā)展的歷史過程中,顯然接受和吸納了很多西藏本土及漢地傳統(tǒng)的宗教元素和實踐內(nèi)容,凸顯出藏傳佛教之本土化的典型特征。是故,對舊譯密咒之文本和教法傳統(tǒng)之形成與發(fā)展過程連同其修習(xí)實踐展開深入的研究,同時把它們與新譯密咒的文本和實踐作細致的比較分析,無疑將揭示藏傳佛教有別于印度佛教的、自主創(chuàng)新的本土化特質(zhì),由此有力推動漢藏佛教比較研究及藏傳佛教中國化研究的進步。《忿怒與大悲》正是在這個研究方向上向前邁進了一大步!
《忿怒與大悲》以藏傳佛教寧瑪派摩訶瑜伽之修部的核心內(nèi)容——修部八教(sgrub sde bka’brgyad)為研究對象,作者首先通過全面梳理與其相關(guān)的藏文佛教歷史文獻,完整地反映寧瑪派所傳修部八教教法之起源與傳承史,并通過對其中重要的敘事材料的解讀,闡明修部八教對以蓮花生為核心的持明崇拜構(gòu)建所發(fā)揮的根本性與決定性作用;其次,作者結(jié)合寧瑪派傳統(tǒng)中關(guān)于修部八教的權(quán)威釋論,對其修習(xí)所蘊含的哲學(xué)義理加以系統(tǒng)闡發(fā),其中也包括對這一摩訶瑜伽修習(xí)系統(tǒng)所體現(xiàn)的阿底瑜伽大圓滿見所作的分析。通過作者對修部八教之修習(xí)系統(tǒng)的深入考察,它無疑可以與國際學(xué)術(shù)界——特別是英國學(xué)者Robert Mayer和Cathy Cantwell夫婦等人對敦煌早期摩訶瑜伽文書的研究成果形成銜接與互補,由此進一步推動和完善對寧瑪派摩訶瑜伽密教傳統(tǒng)的學(xué)術(shù)研究。與此同時,由于以忿怒尊修習(xí)為核心的修部八教正是集中體現(xiàn)影響了整個藏傳佛教的蓮花生崇拜、摩訶瑜伽頗具爭議之誅滅法(sgrol ba)的載體,也是佛教傳統(tǒng)在西藏吸收、轉(zhuǎn)化本土宗教元素的典型,因此,作者針對修部八教展開的研究,也有助于我們更加深入地理解新譯密咒與舊譯密咒的爭論以及藏傳佛教的本土化等重要問題。
筆者對寧瑪派的研究涉及不深,早年曾受談錫永上師(1935—2024)鼓勵,翻譯過寧瑪派摩訶瑜伽續(xù)部之根本續(xù)《秘密藏續(xù)》及其最重要的釋論之一、米龐嘉措(Mi pham rgya mtsho, 1846-1912)所造之《光明藏》,與寧瑪派和寧瑪派研究結(jié)下了很深的緣分。今天,當(dāng)我細讀楊杰博士這部《忿怒與大悲》時,深知他對寧瑪派的研究成就已遠遠超越了我自己對寧瑪派之歷史和教法的粗淺認(rèn)知,但我樂見其成,私意更愿將這本優(yōu)秀的學(xué)術(shù)著作視為當(dāng)年我與寧瑪派所結(jié)之善緣相續(xù)不斷、綿延增上而結(jié)出的一個希有碩果。在此,我鄭重地將它推薦給關(guān)心藏傳佛教的學(xué)界和教界的廣大讀者朋友們。
(來源:《中華讀書報》2025年9月17日第19版)
版權(quán)所有 中國藏學(xué)研究中心。 保留所有權(quán)利。 京ICP備06045333號-1
京公網(wǎng)安備 11010502035580號 互聯(lián)網(wǎng)宗教信息服務(wù)許可證編號:京(2022)0000027



